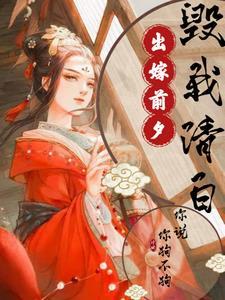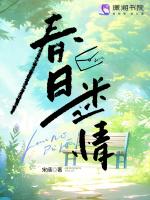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南明崛起 > 第467章 破局者(第2页)
第467章 破局者(第2页)
青铜自鸣钟再次敲响时,胡小利的新房已竖起了房梁。阳光穿过未装窗棂的墙洞,照见梁上悬着的红绸——那是胡大有系上的,祈愿这十年未竟的屋,终能在新日头下,接住第一片青瓦。
老船公撕开靛青粗布衫的瞬间,李奇手中的孔雀石镇纸“当啷”
磕在砚台上。
那道从锁骨斜贯到肚脐的鞭痕蜷曲如活物,在煤油灯的光晕里泛着暗红,每道棱起的痂都嵌着细小的麻丝——是海贸协会特有的浸过桐油的麻绳。
“上个月初七,我在西港码头上摆了三筐蛎灰,刚要雇两个短工补船底。”
老人的指节抠进砖缝,木船常年泡在咸水里的腐木味混着血腥味涌上来,“协会的黄管事带着四个水匪,说修船必须用他们的‘协会匠’,单是‘请人费’就要二十两。
我说祖上三代都是自个儿补船,他们就……”
他突然剧烈咳嗽,瘦骨嶙峋的脊背弓成虾米,咳出的血沫溅在“公平交易”
的状纸上。
李奇的拇指碾过镇纸冰凉的纹路,忽听得窗外竹影晃动,夹着鞋底蹭过青砖的细碎声响。
他朝亲兵使了个眼色,那人立刻抽出腰刀闪进月洞门,不消半盏茶工夫,便拎着个抖如筛糠的账房先生回来——瓜皮帽歪扣在后脑,怀里掉出的烫金名帖上,“海贸协理”
四个金字在火光下泛着冷光。
“军法处的人连夜查了名册。”
次日卯时,莫少红踩着晨露闯进签押房,玄色马褂上还沾着珠江的水汽,“这海贸协会名下有十三家‘分会’,绸缎、瓷器、茶叶各行都有,入会要交‘茶水费’,交易抽‘河沙银’,连码头搬货的苦力都得买他们的‘通行腰牌’。”
他甩下用油布裹着的账册,封皮上“聚宝堂”
三个烫金字已磨得白,“最狠的是‘同业公约’,说什么‘未经协会允准,不得雇用工匠’,老船公们稍不听话,轻则鞭笞,重则凿沉渔船。”
李奇翻开账册,墨笔小楷记得密密麻麻:“绸缎行会馆三月收‘孝敬费’五千两,半数入了广州府刑房典吏的腰包;瓷器帮上月截了艘泉州商船,说‘货不对版’,整船青白瓷全充了‘公产’……”
他的手指停在“码头桩基费”
条目上,下面用红笔标着“分润海防营千总王得胜”
——正是三天前刚给他送珊瑚屏风被拒的家伙。
“要不要现在抄了他们的会馆?”
莫少红按了按腰间左轮手枪。
李奇摇摇头,指腹摩挲着账册里夹着的半张地契——某户渔民为凑“入会银”
,不得不将祖传的避风港地契抵给协会,地契上“永佃”
二字被朱砂涂改成“绝卖”
,画押处按的是个歪斜的血指印,显然是被逼急了的老渔民。
珠江的雾在申时三刻最浓,莫少红带着二十个弟兄扮作盐商,抬着三口贴满“泉州钟表厂”
封条的樟木箱摸进西堤巷。绸缎行会馆的朱漆大门虚掩着,门楣上“公平交易”
匾额裂了道缝,铜匾下的蛛网被夜露坠得沉甸甸的,像张撒开的灭口之网。
“这位公子,打尖还是住店?”
门房哈着腰迎上来,鼻尖凑近木箱时忽然瞳孔骤缩——沉香。
莫少红反手扣住他脉门,将人推进暗影里,二十个弟兄已无声跃上飞檐,堵住前后门。
会馆后堂传来算盘珠子的脆响。山羊胡会正对着八仙桌拨拉翡翠算盘,面前堆着新收的地契,陶朱公像的眼窝里嵌着两粒夜明珠,冷冷照着供桌上成摞的借据。
“入会三千两,月供百两,”
他头也不抬,“若是跑单帮的……”
话没说完,算盘珠子突然飞溅,莫少红的短刀已钉在他手肘旁的桌面,刀刃震颤着出蜂鸣。
“搜!”